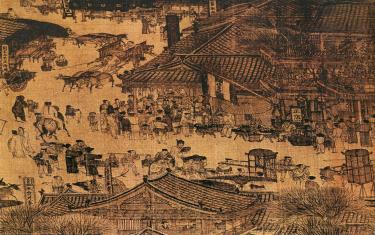青年学者如何看待“去图书馆化”和“图书馆学”改名潮
最近,吴建中馆长接受了徐亚男老师的采访,特别就图书馆学的未来进行了关注。吴馆长十分关注图书馆学改名引发的图书馆地位问题,您如何看待图书馆学改名可能导致图书馆地位下降这一问题?
陶俊:首先感谢您的邀请。我也注意到了吴建中老师的访谈,吴馆是全国知名的馆长和图书馆学家。出于职业使然,他更多从图书馆实务的维度给我们提供了精神食粮。作为高校老师,我更加关注教育本身,正好可以互补一下。
众所周知,图书馆学的前景不是预测出来的,也不是争论出来的。但是,必要的争论和研究有助于改革决策注入更多科学的成分,加快促进共识的形成。
从社会学上看,地位本质是领域贡献的社会外化。高校推进专业改革也有提高教师地位的意味。由于办学涉及到学生、教师、用人单位和社会公共利益,故吴馆提出的问题需要立体来看。首先,也是最为关键的,高校办学目标和图书馆实践不是对应关系,现实情况是,图书馆学毕业生去图书馆只是我们办学的一个子集;馆长所要的图书馆人才往往也不会限制在图书馆学专业,图书馆学专业不可能包打一切。
我认为,图书馆学作为一个学科没有问题,只要有图书馆事业,有研究事业的人就有图书馆学。反过来,图书馆事业需要图书馆人才。但是,需要图书馆人才不等于要以图书馆学专业的名义进行培养。一个专业在高等教育中发展,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支撑。
对照80年代很多专业,今天都消失了。比如无线电等。消失了是因为根据实际发展的需要,它可能以一种更好的方式传承。比如,今天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它在核心课程设置上有很强的图书馆学基因。图书馆人朴实勤劳、甘为人梯,这些是馆员的优秀品德,我相信只要有热爱事业的人,积极服务于高校和公共需要,图书馆地位不会因为图书馆学名称在高校的消失而下降,何况高校仍然有图书情报专硕,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等。我们推进教育改革,通过体制机制理顺馆长、教师、学生和社会的关系,这样更能增强图书馆学青年一代的自信,伴随图书情报专硕质量的提升,我们有更好的人才队伍促进图书馆实务的发展,将更有利于为图书馆事业赢得地位。
Q
看来您是期待图书馆学改名的,记得您有研究过“去图书馆化“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关系,您如何评价国内外的“去图书馆化”和“图书馆学”改名潮现象?
陶俊:从宏观来看,国内外“去图书馆化”主要是寻求办学机会,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更好地承担教育功能。高校校长不会关注是否传承了图书馆学,传承图书馆学是图情档院系基于学科累积和竞争优势的本能,高校更关心图情档院系是否具有更好的办学效益,在更好赢得声誉的同时提高整个学校的声誉。
实践表明,开办图书馆学,首先在招生上就面临危机,如今专业选择自主权逐步下放给学生,象北大、南大的信息管理相关专业都要参与全校社会科学专业的竞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可是拿信息管理专业去竞争,我们的潜在“客户”,也就是广大的学生和监护人面对办学的潜在竞争对手——其它社会科学专业,如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大多时候不愿意选择图书馆学,主动选择图书馆学报考极为有限,如何保证在专业定位上证明图书馆学比其它专业更具优势可以说是无解的;其次,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也遇到了课程体系缺乏时代竞争力;最后,我们还关注学生毕业的长期发展潜力,十年、二十年后,图书馆学专业的校友有持续的竞争优势是教师的渴望。
北大张维迎教授讲,教育不是一锤子买卖,大学办学更像终身制,专业本质是靠声誉吃饭的,毕业校友的成就是办学的硬通货。图情人经常以培养了李彦宏为荣,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涌现更多新时代、更鲜活的李彦宏。高校教师不会奢望毕业生都成为李彦宏,但毕业生的成就是办学最亮丽的名片,也是履行教师责任的结果,换句话说,只有学生挺起了腰杆,教师才有地位。
Q
感谢陶老师对学生成长的关注,李彦宏确实是我们图情学科的骄傲。图情学科教他查找文献,他却鸟枪换炮,进一步抓住机遇开发了百度引擎,引领了中国搜索市场。除了改名的改革方案,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取消图书馆学本科教育,重点发展研究生教育,对此您有何看法?
陶俊:我赞同取消图书馆学本科教育。不仅在于图书馆学是面向图书馆职业的学问,职业实践性强不适合高校本科的通识教育。由于微观在不断变化,高校即使完全按照行业标准去培养图书馆学职业人才,几年下来,馆长也难说合格,因为需求变了。正是由于变化的实践,高校本科的使命在于学习科学理论知识,开展通识教育。
与更接地气、更富于变化的实践不同,科学理论知识相对抽象,位于中上层相对稳定,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抽象思维,让学生有更多可塑性。这也是其它学科专业在市场时代采取的共同方针。正是由于职业实践的多变,而高校人才培养的周期较长,高校专业命名为机械工程,电子信息工程,本质上是淡化具体行业在经济振荡中的微观影响。此外,求职双向选择也要求我们要淡化具体职业定位。
从高等教育使命来看,大学本科生首要目标是促进学生学会独立思考,通过理论学习开发抽象思维,学会联系性地看问题,形成富有社会想象力和综合理论素质的人,为未来打好基础,促进终身学习。由于图书馆学老牌院校大多在重点大学举办,接受重点大学教育应该有引领社会,成为行业中坚的志向,如果重点大学都不参与承担引领社会、开发未来职业的职责,那谁来承担?
Q
如今社会处于转型期,传统岗位面临很多挑战。数字经济时代的确需要有更多学生关注新领域,高校近年来产生了很多专业,可能就是您说的开发未来职业吧。今年由于疫情,各个行业都在缩减岗位,我们图情招聘也了解到,图书馆学的毕业生倍感压力。高校现在好像正面临专业分流,前不久还有学生希望我谈一下专业分流问题,到底该不该选择图书馆学。在这样的环境下,您如何看待图书馆专业的学生不一定愿意去图书馆,图书馆也不一定愿意招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这种错位现象?
陶俊:现在就业压力确实很大,社会面临转型需要我们高校在办学上承担更多责任。学生和教师应是终身的朋友,我们其实特别渴望更多校友回学校看一看,将鲜活的实践带到象牙塔,激发高校教师举办新的专业来引领未来职业的发展。
图书馆学毕业生是否去图书馆不重要,市场经济求职都是双向选择,学生找到能够体现自我价值的职业岗位,老师会由衷的高兴。每一位毕业生都是我们的“产品”,到不同岗位就业就像是更多触摸社会的探照灯。社会需要多元化,我们办学也离不开毕业生不同行业丰富的实践画像。换句话说,错位并不错,只是由于我们的专业名称与图书馆事业对应起来,我们觉得它错位了,这一认识也一定程度反映了图书馆学教学的尴尬地位。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馆长是婆婆,图书馆学的学生是媳妇,高校教师是老公。当前的家庭矛盾,婆婆是最强势的。一方面认为,老公不够给力,课程和研究理论与实践脱节;另一方面,认为媳妇不够给力,实践能力有限,理论高大上也用不上。我想,处理好家庭和谐,三种办法择其一可以实现。一是提高老公的能力,二是降低婆婆的要求,三是媳妇为其他婆婆服务。显然,婆婆不可能降低要求,甚至婆婆本身还面临着数字环境等外部压力,需要更高要求的人才。
正如处理婆媳关系核心在老公一样,如今办学出现了问题,仍然在老公。但是,老公实施课程改革是否就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呢?我们一直在深化图书馆学课程体系的改革,但问题依然在那里。经过多年的实践发现,仅实施课程改革是不够的。如前所述,本科阶段开办图书馆学教育缺乏各种外部政策环境。发展之所以困难,问题远超课程本身:学生报考不积极,专业的规模化程度不足,高校通识教育定位不支持,学生在与其他专业的比较上存有自卑心理,学生求职不受馆长认可,图书馆的总体需求难以消化更多毕业生,职业教育导致学生的长期发展潜力受到抑制等。此外,由于本科紧贴高考,其关注度要比研究生层次高得多,负面作用进一步被放大。大家试想一下,那停办图书馆学本科是好还是坏呢?……
但是,停掉本科不符合高校办学的规模化需求,规模效益对于院系的发展很重要,图情档院系不是缩小规模,而是如何扩大规模,通过增量改革盘活存量的现实问题。没有规模化的学生,不可能引进更多优秀的教师。为此,停办图书馆学本科的同时,需要配套产生具有学科特色的专业,用符合社会需求的优势专业去置换。
改革实践还需加大步伐。学界有提出信息资源管理,但一些人对此持怀疑观望情绪,理由是跟信息管理差不多,没有区分度。可喜的是,近年来业内基于数字人文和公共文化等研究方向有些星星之火。总之,图书馆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专业定位,或者说,媳妇不能为单一的婆婆服务。因此,停办图书馆学本科,探索更多新时代的专业需要学者和学生去呼吁,以期促进不同高校贡献实践智慧。
Q
既要停办本科,又要发展新的专业。我知道您关注图书馆学教育改革很久了,能否结合图书馆学教育的特点,跟我们分享一下图书馆学未来的突破可能在哪里?
陶俊: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坦率的说,我还没有标准答案,特别是国家经济环境和信息环境在变化,其它专业的改革也给我们提出了更多挑战。虽然我也一直关注图书馆教育改革,但我对这个问题的落地设想并不满意。我认为,图书馆学科是社会应用学科,教育应该为国家承担更多公共责任,包括新兴人才、数字转型和文化发展的责任。
如前所述,图书馆学之所以出现问题,根源在于专业定位与时代不够同步,而且过于微观化。突破微观需要从对应的宏观时代环境入手。图书馆事业与我国的文化建设紧密相关。根据经济—文化—政治的金字塔模型,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国家经济起来了,公共治理能力逐步起来了,没有先进的文化,这符合逻辑吗?工商管理、公共管理都在支撑上述两个领域的建设,居于经济和政治中间的文化不可能塌陷下去。由于文化连接着经济和政治,横跨三个层级,伸缩性很强。所以,我认为文化事业一定会加快步伐。数字时代,不仅有传统公共文化,还有数字文化。图书馆、档案馆等有着天然的文化属性,吴建中馆长担任上海世博会顾问、冯惠玲教授引领人文北京和广州记忆建设,李国新、程焕文、刘炜等学者开展的重大项目和研究都具有很强的文化特色。
但这些只是方向,至于如何定位文化类专业仍然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研究,课程体系如何设计也值得探讨。为此,我联合省内同行邀请了业内专家跟我们出谋划策。说到这来了,我索性做一个广告,经过大半年的准备,西北大学将在6月6日举办一场主题为“全国公共文化建设与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的云端学术会议,这个会议邀请了公共文化、文化产业、农村经济和图书馆学教育的部分专家和青年学者一起探讨,感兴趣的老师和图书馆业界同行可以关注,欢迎大家参会交流。
除了文化维度,信息素养也是看待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的维度。图书馆学教育本质是信息素养,因此,网络环境下搜索引擎等工具的使用是信息素养的重要内容。但在移动数字时代,人人都有基本的信息素养,围绕信息获取形成的信息素养面临重新定义。今天的信息素养我认为是程序设计相关基础、数据科学相关基础、基于软件的应用统计基础等编程类、数据类和信息工具类课程。有了这些信息素养,我们再进行更高层的应用或者研究生阶段到其它应用学科从事研究课程学习就有良好的基础。如果相关的毕业生到图书馆去工作,可以通过继续教育学习搜索工具和数据库平台,提高基于检索服务的信息素养。
所以,未来发展新的图书馆学教育不妨跳出既有信息素养的定位,因为信息管理专业已经将信息素养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可以发展文化类相关专业,重点建设好少数专业来形成品牌效应。总的来说,图情档一级学科的核心是信息素养仍然成立,但是内涵需要改变。这有利于我们重塑数字时代信息管理学科的声誉,为壮大信息管理学科群,形成办学的规模效益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如果本科停招图书馆学,有关信息素养的课程可放在图书情报专硕、全校通识教育以及图书馆研究方向课程中去。
Q
陶老师对新的信息素养内涵解读比较新颖,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您刚才有谈到一级学科,我们图情招聘前期也就一级学科改名进行了关注,学生们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那么,一级学科下属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三个二级学科之间是何关系?
陶俊:有关三者的关系,2018年底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39青年沙龙已经讨论很多,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去看相关论文。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中国人民大学钱明辉博士设计的39沙龙LOGO,三者已然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学术共同体。正是因为三者的联系性,历史上曾出现图书馆、情报机构和档案馆的合并。从我国的人才培养历史来看,这三个专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上个世纪50-70年代计划性强,图书馆、情报所和档案馆属于不同部门,计划时代办学为不同部门输送人才进而形成专业或者学科。但是,在80年代以后国家逐步走向市场经济,各学科专业大多实施“宽口径、厚基础”的调整,以应对求职不包分配、市场双向选择的需要。图书馆学、档案学在改革火红的年代坚持了下来,情报专业顺应了改革,产生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从有关文献来看,当时的情报人既有高兴的,也有很多失落的。不管怎样,今天回看历史我们应该感激情报学人,包括实施改革的图书馆学前辈们,它使得图情档的人才培养更加多元化,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为情报学、图书馆学和档案学输送了大量研究生,这些改革进一步为今天的转型探索打下了基础。当然,历史不会重演,图书馆学的坚持也有很多积极的方面,比如,我们与行业的联系相比管理学其它学科紧密得多,涌现了像吴建中、张晓林、程焕文、朱强等一批既有丰富学识又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优秀馆长,我们还基于图书馆学大力发展了公共文化研究,这些都为图情档学科和教育注入了活力。
Q
听您这么说,图书馆实务者和高校办学是彼此成就啊,我们图情招聘连接着你们两家,你们可谓是我们的“股东”和“衣食父母”啊。期待双方就人才培养和利益诉求达成共赢。
陶俊:您太幽默了!的确,我们是供需关系,也是学术共同体。实务界的不少实践话题给高校的理论探索提供了丰富素材,但我们也有自己的苦恼:高校教师成果受到图书馆实务者的批判是不争的事实。我们都知道,学界确实有理论研究和实践脱节的现象,但一些对实践有关照价值的学术成果也难为实务者所关注,学者强调普适规律问题和馆长热衷微观实务问题存在供需矛盾。这客观上削弱了学者关注图书馆实践的兴趣。就教育而言,强调关注实践的同时,要透过实践看理论本质,这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如果双方达成共赢,一项选题至少要包含三点:一是有对重要实践的干预潜力,二是实务者有着本能的引智诉求,三是学者能体现长期的理论担当。在这种约束下,学者该研究什么问题呢?
Q
今天受益匪浅,我们平台一直渴望有更多老师就热点话题参与交流,感谢您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陶俊:我更要感谢你们。没有您的邀请,我不会马上想到这些问题,这也推进了我的研究工作。3月初借助贵平台开展新信息管理互动,我就意外了解到,学生们对停办图书馆学专业很关注,有关留言的点赞数位居前三。但正所谓知易行难,推进教育改革非常不易。除了开展理论探讨、回应典型争论,也离不开兄弟院校广泛实践,此外,还受到现实情境约束和外部博弈的影响。期待更多同仁参与到图书馆学改革实践中来。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陶俊,男,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现为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仲英青年学者。长期关注图情档教育改革研究。著有《声望关联、文献工作演进与图书馆学教育改革》等学术论文,近作《信息管理学科竞争力与结构改革》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9年5月出版。
来源:图情招聘
转载自:https://mp.weixin.qq.com/s/FVivwA9p8tnVY0Jbt3ZCjQ